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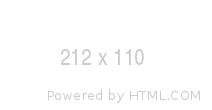
用mions检查金字塔
 19。 04。 2024
19。 04。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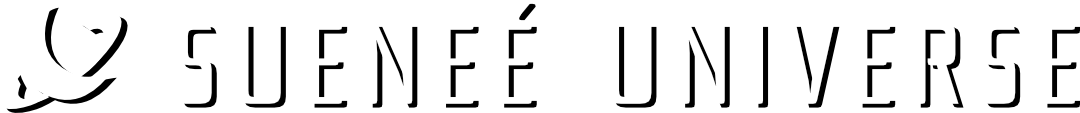


 4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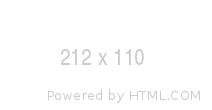
 19。 04。 2024
19。 04。 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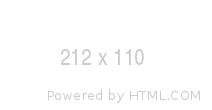
 18。 04。 2024
18。 04。 2024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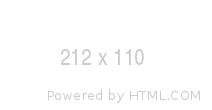
 17。 04。 2024
17。 04。 2024
 6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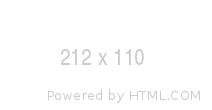
 16。 04。 2024
16。 04。 2024
 5
5
 20。 05。 2023
20。 05。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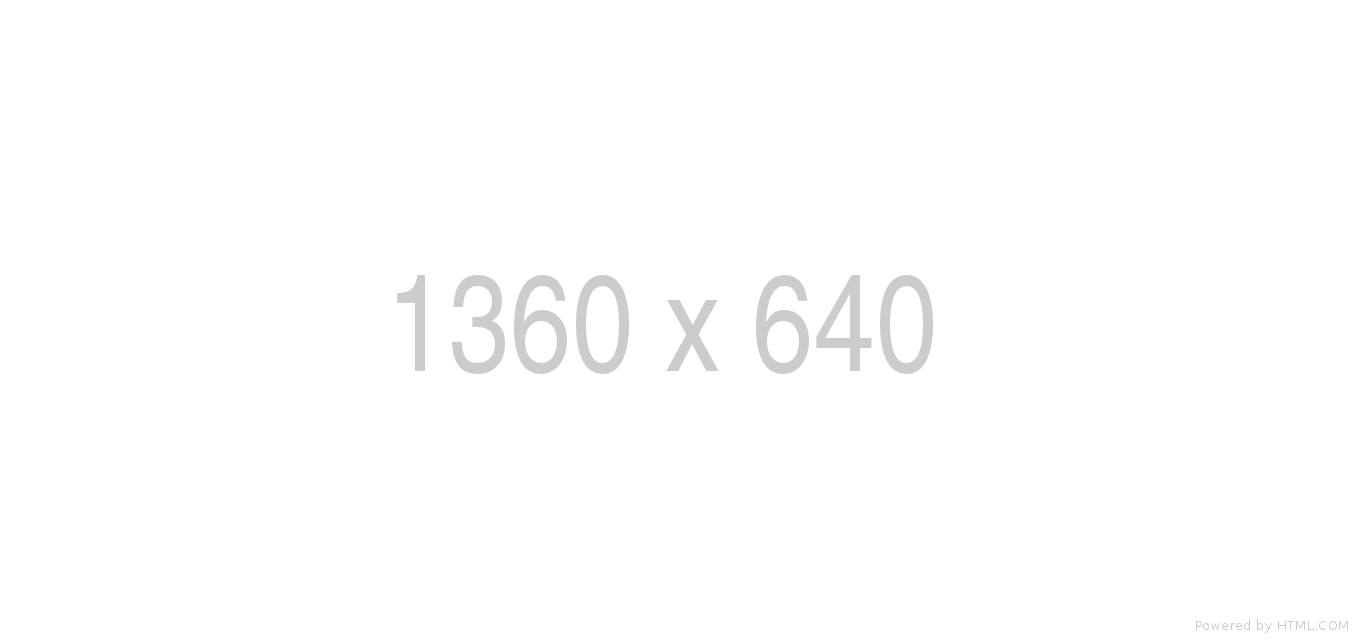
在经历了6万年的无聊之后,自从上一个前辈与黑猩猩一起进化以来,我们物种的进化崛起,使我们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 它发生在不到100年前,顺便说一下,这是在解剖学上现代人进化了很长时间之后。 不到000年前,甚至不到100年前,我们以某种方式变得有意识,成为了完全的象征性生命。 这种巨大的变化被描述为人类行为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步,并且与世界各地重要的超凡岩画和洞穴壁画的出现紧密相关。
在过去的30年中,来自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科学家率领教授。 大卫·路易斯·威廉姆斯(David Louis Williams)和其他许多人指出,当我们的祖先遇到有远见的植物和新生的萨满教义时,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引人入胜的革命性可能性。
当我们检查洞穴壁画时-我没有时间详细讨论-从许多细节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艺术起源于意识,视力改变的状态,而植物和真菌(例如红色毒菌或psilocybin蘑菇)可能与这一突然而根本的变化直接相关。 。
当我对意识的奥秘感兴趣时,我开始在亚马逊探索这种机会,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发现萨满文化中喝着有远见的饮料ayahuascu,其主要成分是二甲基色胺或DMT。 在分子水平上,它本质上非常接近psilocybin。 但是,仅在通常吸烟的西方国家遇到的DMT并没有口服效果。 在胃中,我们有一种称为单胺氧化酶的酶,可消除DMT的作用。 但是,在亚马逊,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们说这是鬼传给他们的。 ayahuasca中包含的DMT来自亚马逊河中称为chacruna的植物的叶子。 这些叶子与爬山虎混在一起,爬山虎是150万种亚马逊植物和树木中仅有的一种,其中含有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可以关闭胃中的酶。 因此,可以将这种独特植物组合的汤剂中的DMT口服,并在000小时内朝着非凡的领域朝圣。
但是喝阿育吠陀没有意思。 hua药的汤真是令人作呕。 这真是令人作呕,闻起来绝对可怕。 喝完杯后,大约45分钟内,您会发现自己出汗并且胃部不适。 不久,您可能会呕吐,腹泻。 因此,没有人会消遣。 我想补充一点,我认为不应将迷幻药用于娱乐。 他们对人类负有更为重要和重要的使命。 所以这不好玩。 但是人们决心一遍又一遍地使用ayahuasca-确实需要决心-因为其对意识水平的非凡影响。
其中之一与创造能力有关。 秘鲁阿萨瓦斯萨满的萨满教徒的图像中清楚地显示了阿亚瓦斯卡的创意宇宙诱因,例如巴勃罗·阿马林(Pablo Amaring)描绘的多彩,鲜艳的色彩和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 这些创造性的刺激也影响了西方艺术家。 阿亚瓦斯卡(Ayahuasca)从根本上影响了许多西方画家,他们也描绘了他们的愿景。 在他们的画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普遍分享的经历,即与显然聪明的生物的相遇,他们通过心灵感应与我们沟通。 我并不是说这些生物是真实的或虚幻的。 我的意思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在阿育吠陀体验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与他们会面-并且多数时候是阿育华斯卡自己的精神,治愈我们的阿育华斯卡母亲,尽管她是我们这个星球的母亲,但她似乎会立即他个人对我们很感兴趣,他想治愈我们的疾病,帮助我们成为最好的人,纠正导致我们误入歧途的错误或错误行为。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谈论不多-ayahuasca在治疗对海洛因和可卡因等硬性药物有害的成瘾方面非常成功。 雅克·马比特(Jacques Mabit)允许海洛因和可卡因成瘾者在秘鲁的塔基瓦西诊所接受每月治疗,并与他们进行了12次疗程,在此期间他们与阿亚瓦斯卡母亲会面。 会议导致吸毒者渴望戒除可卡因和海洛因,其中超过一半的人完全摆脱了瘾,不再陷入瘾,甚至没有戒断症状。
盖博·马特(GaborMaté)博士在加拿大受到了同等的待遇,直到他的工作被加拿大政府以ayahuasca本身是非法药物为由而停止。 我和她有亲身经历。 我没有沉迷于可卡因或海洛因,但我连续24年不断吸食大麻。 我开始抽大麻,也使用了汽化器,但总之,我经过24年的不断测试。 我很喜欢这种情况,并发现它可以帮助我写作。 有时候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当我初次见到ayahuasca时,我已经吸了16年大麻,而ayahuasca几乎立即开始告诉我大麻不再给我任何东西,我让其他人感到不舒服并向他们的脚扔棍子。 当然,我多年来一直不理会这些信息,而每天又要生气16小时。 但是ayahuasca警告我的负面行为越来越严重。
我不想以任何方式投放大麻,而且我认为每个成年人都有选择以自己的自由意愿抽烟的主权。 但是我过度和不负责任地使用它,实际上滥用了它。 我变得越来越偏执,嫉妒,占有欲和可疑,我不合理的愤怒使我不知所措,让我心爱的伴侣桑莎的生活更加痛苦。 当我在2011年XNUMX月再次遇到ayahuasca时,我得到了来自Ayahuasca妈妈的绝妙踢球。 我经历了难。 这是我一生的回顾。 ayahuasca被称为死亡爬行者并非巧合。 她向我展示了我的死亡,我发现如果我死了而死后没有改正我的生活错误就到达了我们所去的地方,那将是非常糟糕的。 我真的和阿亚华斯卡妈妈一起经历了地狱。 它使我想起了希耶洛缪缪斯·博世(Hieronymus Bosch)创作的地狱。 真可怕根据古埃及人的说法,这里也有点像乌西尔神(Usir)审判的地方,灵魂在神面前被称重,真相,正义和宇宙和谐。
我发现我所走的道路,滥用大麻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将使我被判定为“不令人满意”,并且显然在来世被摧毁。 因此,当我于2011年XNUMX月返回英国时,我戒掉了大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抽过烟,这可能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我提醒您,我在谈论我的个人经历,我不对使用大麻的其他方式发表评论。 仿佛一块石头从我的心脏上掉了下来,我在许多方面都感到自由。 相反,我的创造力一点都没有停滞,相反,作为一名作家,我更有生产力,更有创造力,更专注,也更有效率。 我还开始解决大麻暴露出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我正在慢慢成为一个更关怀,更爱,更积极的人。
整个转变-对我而言,这确实是个人的转变-是由于我遇到了阿亚华斯卡母亲为我带来的死亡。 我问自己一个问题:死亡是什么? 我们的唯物主义科学减少了所有重要的事情。 根据西方唯物主义科学,我们只是肉体,我们仅仅是身体,所以一旦大脑死亡,就意味着我们意识的终结。 死后没有生命,我们没有灵魂。 我们只是烂了,它结束了。 但是,许多真诚的科学家应该承认,意识是科学的最大奥秘,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它是如何工作的。 大脑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中,但我们不知道如何参与。 大脑可以产生意识,就像发电机产生电一样。 如果您坚持这种范例,那么您当然不相信死后的生活。 当产生器破裂时,意识就在那里,但是这种关系(神经科学并不排除这种关系)更像是电视信号与电视之间的关系。 并且在那种情况下,如果电视坏了,电视信号显然会持续存在。 这是所有精神传统的范例:我们是不朽的灵魂,他们以这种物质形式暂时物化,学习,成长和发展。 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个奥秘,那么唯物主义的还原论科学家就是我们应该问的最后一个。 他们对此无话可说。
让我们转向古埃及人,他们的最聪明的大脑已经与死亡打交道了3000年,我们该如何生活以为死后遇到的事物做准备。 古埃及人以超凡的艺术表达了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仍然在情感上影响着我们,并得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结论,即灵魂在死后仍活着,我们将为我们的所有思想,行为和生命中的每一项行为负责。 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地利用这一宝贵的机会-诞生于人体内-并充分利用它。
但是古埃及人不仅在研究死亡之谜方面训练了他们的想象力。 他们非常珍视梦想,今天我们知道他们使用了有幻觉的植物,如致幻的蓝莲花。有趣的是,古埃及的生命之树最近被确定为相思树,其中含有高浓度的DMT,二甲基色胺,与发现的活性成分相同。 ayahuasce。
但是,很难想象有一个社会比我们的社会与古埃及社会有更大的不同。 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反对有远见的国家。 如果我们想得罪某人,我们称他们为梦想家。 在古代社会,这是一种认可。 我们已经建立了庞大而强大的官僚机构,侵犯了我们的隐私,敲了敲门,逮捕了我们,将我们送入监狱-有时长达数年-甚至拥有少量的可吸入性泛素或诸如DMT的物质,无论是可吸入形式还是阿育吠陀汤。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我们今天所知,DMT是大脑中的天然激素。 它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体内,唯一的问题是,由于研究不足,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工作的。
但是,我们的社会并不反对这种改变的意识状态。 毕竟,这种不道德的精神病医生协会和制药游说组织正在赚取数十亿美元的处方药,以管理所谓的综合征,例如青少年的抑郁症或注意力不足。
然后是我们社会对酒精的热情联系。 尽管使用天堂带来了可怕的后果,但我们正在将一种最无聊的毒品带到天堂。 当然,我们喜欢我们的兴奋剂:我们的茶,我们的咖啡,我们的能量饮料,我们的糖。 整个行业都基于这些物质,我们重视它们以改变我们的意识。 这些允许的意识改变状态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没有违背我们社会认可的基本意识状态,即一种“问题导向的警觉意识”。 这适用于相当普通的科学方面。 它适用于战争,贸易,政治,但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知道,垄断这种意识状态的社会的潜力是空的。 ¨
此模型不再起作用。 他千方百计地被打破了。 迫切需要寻找其他地方:有目的地追求利润造成的全球性污染的广泛问题,核武器的可怕扩散,饥饿的幽灵,成千上万的人每晚都在挨饿。 尽管我们保持警惕和以问题为中心的意识,但我们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看看亚马逊,我们星球的肺,我们在那发现了许多不同的物种。 古老的森林被砍伐,取而代之的是大大豆来喂养我们制作汉堡的牛。 只有在真正的病态的全球意识中才允许这种可憎的行为。
在伊拉克战争中,我经过粗略的计算,意识到与这场战争六个月有关的问题将由亚马逊的问题彻底解决。 这足以补偿亚马逊地区的人民,因此不必砍伐任何一棵树,他们只能照顾和保护这一惊人的资源。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全球社区无法安排它。 我们可以在战争,暴力,恐惧,怀疑,分裂上花费数十亿美元不受管制,但我们不能齐心协力挽救地球的肺气。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来自亚马逊的萨满教徒现在开始颠覆某种宣教活动的原因。
当我向萨满教徒询问西方疾病时,他们很清楚地看到:“您与精神分离了关系。 如果您不与他重新建立联系,并尽快进行,您将丢下整个纸牌屋,它会落在您的头上和我们的头上。
许多人都听到了电话,现在正去亚马逊喝ayahuasca。 反过来,与阿亚瓦斯卡(Ahuahuasca)合作的萨满教徒穿越西方,通常是秘密地,自担风险地提供汤剂,并试图改变我们的意识。 事实是,阿亚华斯卡将所有神圣,神奇,神奇,无限稀有的生命精髓以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相互联系带给了所有人。 与ayahuasca一起使用时,迟早不能阻止此消息深深地打动我们。 但是,请不要忘记,ayahuasca并不孤单。 它是古老的有针对性的,仔细的,负责任的意识改变的全球系统的一部分。
研究人员最近发现,古希腊Eulezine谜中使用的kykeion最有可能是一种迷幻饮料,而Vedas中的豆浆则可能是红色的伞菌饮料。
我们在古埃及人的生命之树上拥有DMT,并且我们知道世界上仍然存在的萨满文化。 所有这些都与意识状态有关,其目的是帮助我们实现平衡与和谐。 古埃及人称其为宇宙大主教。 让我们记住,我们在地球上沉浸在物质中的使命首先是一条旨在灵魂发展和改善的精神道路,这条道路可以使我们回到人性的基础。
在这里,我行使着来之不易的言论自由权,呼吁并承认另一项权利:在我的意识中享有成年人主权的权利。 我们的社会正在发动一场意识战,除非成年人有权独立决定如何处理自己的意识而又不伤害任何人,包括负责任地使用远古神圣的有远见的植物,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对我们的社会来说,把我们的民主形式强加给世界是不值得的,同时毒化社会的血液,剥夺个人的知情权。 也许通过维持这种状况,我们甚至否认自己是我们发展中的另一个绝对基础的步骤-谁知道,我们可能在无视我们的永恒命运。
谢谢各位来宾。 谢谢。 谢谢。